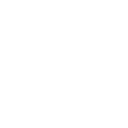


應急救護是在專業急救人員到來之前,由應急救護員(第一目擊者)志愿為傷病者提供及時的初級現場緊急人道救護行為。公司為有效保護員工的生命和健康,提高員工自救互救技能,為大家生命安全增加一份保障,1月10日公司組織開展急救技能培訓。
以下文章摘自鳳凰周刊
救心時刻——內地心臟急救現狀
對于難以預測而又普遍發生的心臟驟停,內地亟需普及公民急救知識、推廣設備、清除各種阻礙。急救不可只依賴120!
記者/王彥入盧伊關珺冉
一通持續了10分40秒的電話,將一條生命從鬼門關拉回。發生在遼寧葫蘆島的這一幕,近日為輿論所關注。
被救助的是一位60歲男子,他突然昏迷倒地,失去呼吸,沒有脈搏。家屬反應過來,立馬撥通電話,向120求救。
接起電話的是葫蘆島市急救中心調度員李紫慧,憑借過往經驗,她敏銳地判斷,這可能是一位心臟驟停的患者。若判斷無誤,對于這類患者,搶救的黃金時間僅有4分鐘。
調度了距離現場最近的救護車后,李紫慧沒有掛斷電話,她朝聽簡那端的家屬囑咐,“仔細聽好,我現在教你怎么做胸外按壓。”
按照李紫慧的指導,家屬開始依步驟為患者進行心肺復蘇,直至急救醫生趕到現場,這通搶救生命的電話總共持續了10分40秒。盡管家屬未受過專業訓練,進行心肺復蘇的姿勢不夠準確,但在120趕往現場的空窗期,保證了患者的肺部呼吸換氣與心臟的泵血,在醫生趕到進行專業急救前,保住了患者性命。
不同于其他病癥的可預測性,發生心臟驟停的人,可能就是你我。“他不是躺在病床上的人,他就是走在路上的人,看上去很正常,不覺得他是病人,但可能發生無預期的心臟驟停。”上海市浦東新區醫療急救中心主治醫師馬俊杰描述。也正是因為它發生的非預期,很難保證醫療力量在短時間內就位。在中國,如果有人發生心臟驟停,被救活的機幾率不到1%。
無疑,這名男子是幸運的,因為搶救及時,成為了幸存的1%。而更多心臟驟停患者,由于得不到及時的救治,錯過黃金搶救期,與世長辭,留下一地遺憾。
相較于發達國家在急救方面的表現,內地有著不小的差距。數據顯示,美國每年約有40萬心臟驟停病例,整體搶救成功率約為10%。在一些設施完備的大城市,比如紐約、西雅圖,被救回來的幾率可能在50%以上。如果你“幸運地”倒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里,被救活的概率甚至高達75%。
傲人的生命數據背后,是數量龐大的急救員、配備齊全的自動體外除顫器(以其下簡稱“AED”)和全民普及的急救意識。
只等120,相當于“等死”
10秒,意識喪失突然倒地。
30秒,全身抽搐。
60秒,自主呼吸逐漸停止。
3分鐘,開始出現腦水腫。
6分鐘,出現腦細胞死亡。
8分鐘,進入“植物狀態”腦死亡。
黃金8分鐘,分秒之差就將決定生死。
“任何人、在任何地方,均可借助你的雙手開始實施心肺復蘇。”1960年,美國霍普金斯的三位學者在JAMA雜志上發表里程碑式的論文《閉式胸部心臟按摩》,論證心外按摩的有效性。也在同一年,馬里蘭醫學會議正式提出胸外按壓和人工呼吸聯合應用。
導致心臟驟停的原因有很多,包括以缺血性心臟病為代表的各種嚴重的器質性心臟病,各種原因引起的心力衰竭等。生活不規律、日夜顛倒、工作壓力大等,都會成為潛在威脅。面對心臟驟停患者,每延遲急救一分鐘,成功率便下降百分之十。若什么也不做,只等120,待十分鐘后,120抵達,患者可能已無搶救機會。
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發布的《中國心血能管病報告2014》顯示,全國每年發生心臟性猝死預計為54.4萬。這意味著,平均每一分鐘,便會有一個人被心臟性猝死奪去生命。這其中,5%的猝死發生在醫院內,近七成發生在家中,還有約1/4的病人發生在其他場合。在醫院以外的猝死病人中,65%死于發病后15分鐘內。如能掌握急救技能,并及時實施,這些生命本可以挽救。
但在我們生活中,常常看到的正是這樣的場面:有人倒地、呼叫120、等待120、眼看120將人拉走,如若發生意外,便將責任全數推給120,到場太慢,救治不力,都是熟悉不過的說辭。
長期盤旋于公眾腦海中的急救意識幾乎可以等同120三個數字。
但實際上,更大范圍的院前急救,還應包括現場急救,“不單純是醫院的醫療力量來到現場,而是現場周邊的人,即刻開始行動,施予救助。”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、微博大V“急診夜鷹”王西富解釋,所謂現場急救,用英文翻譯,便是“ First aid”。也有人賦予它更具畫面感的詮釋:車前急救一一救護車到來之前的急救。

2014年9月5日,北京,中國建筑安全培訓體驗中心內,接受心肺復蘇培訓的人員
也就是說,院前急救可分為兩段,一個是到達醫院前實施的現場救治,一個是轉運途中緊急救治和監護為主的醫療活動。
上海市浦東新區醫療急救中心主治醫師馬俊杰對此有更形象的解釋,他管前者叫“公眾急救”,交付于公眾,填補救護車到達前的時間空缺,而后者“專業急救”才是我們熟知的救護車監護環節。
但匱乏的急救意識,使公眾往往跳過現場救治”的前奏,直接寄希望于“專業急救”,從而耽誤時間,影響救治。
“救護車不可能說二十秒就到。它總得需要十幾分鐘,甚至更長時間。即使三五分鐘到達現場,那真是住在醫院隔壁,(就算)住在醫院隔壁,你還得看樓層高低,得爬樓啊。”王西富說,對于不緊急的創傷,尚且等得起,如果是黃金救治時間僅四分鐘的心臟驟停,“等醫生,基本等同于等死。你送到醫院去,基本等同于送死。”
王西富說,從業多年,院醫外心臟驟停患者依靠撥打120,等待醫生到場并成功救治康復出院,“沒有一個成功的”。
“你想想,心跳停了,每延遲急救一分鐘,成功率便下降百分之十。那你十分鐘之后,醫生到了,那不就是收尸體嘛。”王西富說。
這不是危言聳聽。
2016年6月29日,天涯社區副主編金波結束一天工作,下班回家。不久后,在北京呼家樓地鐵站暈倒,隨即失去意識。現場先后有三人出手相助,但最終無濟于事,送至朝陽醫院時,已無生命體征。據朝陽醫院急診科醫生介紹,金波屬于突發性心臟病猝死。
尤其讓人惋惜的是,朝陽醫院距離事發地呼家樓地鐵站僅兩公里左右。“所以我們要走出一個誤區,急救,是每個人的事情,它不單純是醫療人員的事情。尤其對于一些分分秒秒都會死人的狀況,那更是等不得醫生。”
知道不等于掌握
金波暈厥倒地,有兩位乘客對其進行了心肺復蘇,之后,有一名自稱是急救醫生的外國女子也參與到救助中去。
部分現場急救視頻在網上發布后,有網友提出質疑,稱事發現場的急救行為不專業,地鐵工作人員也缺乏必要的處置。
王西富也以“急診夜鷹”的名義,在公號文章里提出幾點質疑:視頻時長2分30秒,胸外按壓僅僅占據23秒,按壓了55次,而更多的時間花費在人工呼吸上,以及猶豫和商量之中。

2017年2月22日,春節過后,上海地鐵幾個人流較大換乘站開始出現標注為“AED”(自動體外除顫儀)的設備。
對于突發的心臟驟停,高質量的胸外按壓尤其重要。按壓位置在胸部正中,每分鐘100-120次,深度5-6厘米,直至患者蘇醒,或救護車抵達現場。但現實生活中,施救時做到這點并不容易。
首先,大部分公眾不具備急救意識不懂急救。其次,“大家有了急救的觀念,但是事情發生后,你光有觀念,沒有用,你得有活兒。”全民互助急救平臺“第一反應”創始人陸樂感慨,“我們好像是一聽就懂,一學就會,但你真的碰上了,完全不知道怎么辦。因為一放就忘,一用就亂。”
陸樂的這一番感慨,要追溯回2012年2月5日。當日,在深圳戈壁挑戰賽預選賽賽道上,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友劉文,眼看著勝利在望,卻沒能堅持到撞線那一刻。在距離終點兩百米處,喘著粗氣的劉文突然暈倒,生命就此定格。
就在事件發生一天前的2月4日5時15分,劉文在騰訊微博寫下:“真困”。當晚21時52分,他再次更博,“天啦,今晚別再讓我失眠了,很痛苫。”5日5時19分,他又寫下“還是困”三個字。
誰也沒想到,幾小時后,在戈壁挑戰賽的終點前,劉文突然心臟驟停,與世長辭不再被睡意困擾,這一次,他長眠不醒。劉文倒下時,其他參賽隊員不斷聚攏過來,他們都想救他,用盡各種方式,無一奏效。而被大家寄予厚望的120救護車到達現場時,已回天乏術。事實上,開賽前各隊參加過不同程度的急救培訓講座。
“那個時候,我已經在中歐做了大概兩三年的(急救)公益講座,有的(參賽隊員)在我的課上聽過,有的在紅十字會學過,大家都有觀念,學過一點。
但事情發生后,大多數人都只是略知皮毛,怎么做卻沒人會。這令同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友的陸樂頗受觸動,“很痛心嘛,這么優秀的同學們,要錢有錢,要智商有智商,要體力有體力,還能跑馬拉松。但是當身邊的朋友倒下時,我們是如此的無助,無力。”陸樂放慢語調,“不是無為,真的是有為,但是這個為’,是一個無效的‘為’。”
校友去世刺痛了陸樂。作為一個極限運動愛好者,九十年代初,陸樂便已取得國際認證的急救資格證。他隱約覺得,自己應該做些什么,“從那個時候,讓我開始覺得有責任,不是去跟大家講講故事,不是去跟大家講講觀念,而是讓大家真實地擁有(急救)這個技能。”
當年年底,“第一反應”成立。此前國內還沒有致力于賽事保障和急救培訓的民間機構。之所以專注于賽事保障,緣于體育賽事中心臟驟停事件的高頻發生。
據媒體報道,中國田協的相關數據統計,在近三年(截至2017年)時間里,國內的馬拉松賽事中已經有超過16人猝死,這些參賽者均是跑步中出現心臟驟停經搶救無效而死亡的。類似案例一次次敲響警鐘。
為了在中國普及這項技能,從2013年開始,陸樂創立的“第一反應”開始推廣美國心臟協會(以下簡稱“AHA”)的急救培訓:8小時課程,導師學員一比六,從急救知識到急救技能。課程中理論學習與實踐練習結合,并嚴格考試,通過考核者方能取得AHA頒發的急救證書。
有人嫌“八小時(培訓)太長”,他們找到陸樂,尋求捷徑,“能不能給我們弄個一小時(的培訓),就講講急救知識。
他們將急救視為“老師站在講臺上講,下面幾百個人坐著聽聽就行”的“知識”,而沒有意識到,急救實際上是一門技能,“就像考駕照,駕車學的是什么,是駕車技能。”這個也一樣,別人發生危險,你得知道怎么動手去救。而不是光知道,不會用。”北京玉山急救培訓導師田燃一直強調。
也有人對此心存敬畏,他們報名學習,考取證書。至今,“第一反應”已培訓上萬人。其中一部分經注冊,成為了“第一反應”志愿者。
做志愿者并不輕松,每隔三個月需要參加一次公益活動,“每三個月,你花一天時間,參加一次公益活動,就溫故而知新了。”陸樂介紹,長此以往,反復訓練,志愿者方能形成肌肉記憶,將學來的技能變為已用,“假使幾年后,你身邊的人遇到危險,你不會亂,你能在一個很好的狀態下去救別人的命。”這是對“技能”的鞏固事關人命,斷不可輕心大意。
截至2018年3月7日,“第一反應”的志愿者們已為284場賽事提供賽道保障,為1230000名跑者保駕護航。在過去幾年間發生的12起心臟驟停事件中,成功救活11人,救活率保持在92%以上。
電話指導也能救人
急救這門技術是如此的普通但又專業,即便那些擁有執業資質的醫護人員也未必掌握合格的院前急救技能。
2017年12月底,中國醫學科學院、北京協和醫學院臨床博士后招生考試進入第三日,心肺復蘇是這場持續五日大考的考核重點,但成績卻不盡如人意。
心肺復蘇是臨床醫生的基本技能,但成績好的幾乎沒有我們的學生,這說明我們在教學培養中存在很大問題。”這讓參與監考的一名醫生大為光火。
心臟除顫開始時間每晚一分鐘,可以挽救回來生命的可能性就降低7%-10%。普通市民按照電話的CPR口頭指導操作,直到救護車到來之前,不浪費一秒進行急救,可有效防止救活率降低。
急救培訓人員也有類似的感受,他曾接待首都醫科大學的一位專家參與急救培訓,卻發現對方實施心肺復蘇時有很多錯誤。“還有些急救人員并不清楚什么情況才能做心肺復蘇,很多病人暈倒后還有呼吸和意識,卻被做了心肺復蘇,活人都可能被摁死了。”
讓全民都掌握急救技能,成為稱職的專業急救人員,或許過于理想。另一種更為實際的辦法則是通過醫療急救電話的即時指導,就像葫蘆島那位被救回來的60歲男子那樣。
世界急救的救活率最高的地方,是著名城市西雅圖所在的金縣(美國行政區劃中,州下一級為縣)。2013年,金縣心臟驟停的救活率高達62%,同一時期的紐約,芝加哥等大城市則只不到10%。時任縣長曾自豪地說:“今天在金縣被救活的人,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能保住性命了。”
在這里,金縣75%以上的市民都接受過心肺復蘇術(CPR)的訓練課程,但如果你撥打急救電話,也會有專業人士在線口頭進行心肺復蘇的同步指導。市民所接受的訓練也是從先撥通911開始、再迅速判斷心肺功能是否停止、接著按照口頭指導進行急救。2014年金縣年度報告顯示,在成功實施CPR的72%案例中,41%是經過急救指令室的口頭指導完成的。
美國急救醫學會議也曾在一份研究報告中,肯定了心肺復蘇的電話指導對急救救活率提高的直接貢獻:“心臟除顫開始時間每晚1分鐘,可以挽救回來生命的可能性就降低7%-10%。普通市民按照可電話的CPR口頭指導操作,直到救護車到來之前,不浪費一秒進行急救,可有效防止救活率降低。”
救命神器AED
金發碧眼的“安妮”們平躺在水冷的地板上,他們沒有意識,失去呼吸與心跳,亟待被好心人救起。
突然,激烈的鼓聲不斷,十余名熱心老人立刻兩兩一組,交疊雙手,以跪姿聚攏在“安妮”們身旁,他們必須和著飛快的鼓點,垂直擠壓“安妮”們僵硬但富有彈性的胸腔,不能過深,也不能過淺。隨后,他們還要輕抬“安妮”們的頭部,捏緊鼻子,用嘴封住其口,一邊用力吹氣,一邊觀察期胸腔起伏。
30次心臟按壓,再接2次人工呼吸,循環往復。但鼓聲未歇,便有人脫離了節奏,老人們越發走形的動作帶出粗氣和汗珠。
這是北京協和醫院的急救培訓活動,參與者需通過觀摩美國心臟協會教學視頻和急診科專家指導,習得心臟與呼吸驟停的判斷方法和急救操作。躺在地上的,只是數具模擬真實人體結構的橡膠人,“安妮”是醫學生賦予他們的呢稱。
66歲的北京老人陳朗也在其中。4個多小時的培訓中,所學內容只有一項心肺復蘇。這也是陳朗最想掌握的一項技能。他與老伴均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腦血管疾病,此前,“掐人中”和“服救心丹”是老兩口僅有的“急救技能”,他們期待萬一遇到突發情況,能靠新技能破解危局。
2016年,內地啟動全國心肺復蘇進億家精準健康工程,旨在5年內,向2億人口普及心肺復蘇,每人培訓5戶家庭,以提高急救技能的普及率,會救進而敢救。
“心肺復蘇不光是當場學會就能掌握的,只有形成肌肉記憶,才能在突發情況下,像調動本能一樣正確施用。”前述急救培訓人員告訴《風凰周刊》,目前,多數培訓班均為一次性授課,當堂學會的很多技能,數日后便會被多數學員遺忘。盡管也有部分培訓班允許學員有償或免費反復練習、但由于耗費時間和精力,收效并不理想。
陳朗深由同感,剛完成培訓的那幾天,他時常在家里向老伴傳授心肺復蘇經驗,但時間久了,記憶越來越模糊、他甚至想不起應當摁壓的位置和頻率,只能在網絡上搜索教學視頻、照貓畫虎。
相比操作難度和致傷風險更大的心肺復蘇,自動除顫儀對普通公眾參與院前急救的門檻更低,成功率更高。其作用原理為,在極短時間里,以強電流通過心臟,使心臟恢復正常心率。
在國外,人們對自動除顫儀習以為常。早在1990年代,美國就通過法案,實行“公眾可獲取的除顫儀”計劃,即在美國公共場所安裝設備、確保10分鐘內即可獲得。并對普通民眾進行訓練。但對內地而言,這仍是一個極為新鮮,甚至有些意義不明的產品。
陳朗此前就有這種感受,但經過培訓,他至今對這款“傻瓜式”急救儀器印象深刻,其大小與兩本字典并放相仿,機身只有一塊屏幕、2個摁鈕和2塊電極貼片。操作時,他只需按下開關,便可跟隨中文語音提示,按儀器圖示,粘好貼片,由機器分析病人是否需要電擊,并發出電擊,直至病人心跳恢復,整個過程十分簡便,沒有任何難度。
這是一款專供普通民眾使用的心臟除顫設備,便攜且易于操作。即便是毫無急救知識的普通人,多可在30分鐘內學會使用,心肺復蘇成功率可提高2-3倍,病人生存率也將提高近50%。由于大部分院外心臟驟停,都為心源性心臟驟停,其表現便是室顫。AED的電擊除顫是針對其最有效的急救方式。數據顯示,心臟驟停發生后,除顫每晚實施一分鐘,生存率下降7%。
相比操作難度和致傷風險更大的心肺復蘇,自動除顫儀對普通公眾參與院前急救的門檻更低,成功率更高。其作用原理為,在極短時間里,以強電流通過心臟,使心臟恢復正常心率。
在諸多歐美國家,急救知識普及率高,AED在公共場所的配置率也高,危險發生時,普通民眾可以就近獲取,趕在專業急救人員到來之前,為心臟驟停者盡早實施電除顫。比如傳播甚廣的中國醫生美國公園救人案例。
2015年3月,朝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唐子人醫生在美國圣地亞哥海洋公園游玩,一位老太太突然倒地,離唐子人僅十米遠。他快步上前,判斷情況并表明身份,征得家屬同意后,開始為老太太做胸外按壓。大約是按壓了十分鐘左右,就有人拿來了AED,一塊兒協同操作下,給患者除了兩次顫。之后,患者自主呼吸恢復,慢慢就正長呼吸了。”
此事經網絡傳播,唐子人意外走紅。被網友贈予“中國好游客”“中國好醫生”的稱號。但唐醫生表示,之所以能夠最終挽救老人的生命,是因為美國公園內到處安放的AED,對搶救起到了關鍵性作用。他希望,媒體別將焦點放在他個人身上,而是應該由此事關注到中國的急救現狀,提高大家對AED的重視。
用AED成功救人,“第一反應”的志愿者也有范例。
2015年3月15日9時17分,無錫半馬20.3公里處,一位選手無預期暈厥倒地。三四百米外,作為“第一反應”志愿者的馬俊杰,正在賽道巡邏。他站在路口拐角處,向兩側張望,留意到一股人群逐漸圍攏在一起,他意識到,“可能發生事情了”。
毫無遲疑,他向人群跑去。發病的選手正直挺挺地躺在地上,臉色蒼白。萬幸的是,跑者暈倒時,另一位志愿者僅離他十幾米,后者立馬上前,按照培訓所學,確認病例無反應、無呼吸,便依步驟開始進行心肺復蘇。
“我們的要求是,心肺復蘇兩分鐘就要輪換一人,我跑過去后,剛好接替前替前一名志愿者,繼續做胸外按壓。”馬俊杰回憶。
直到負責AED的隊員攜AED到達現場,他們立即打開AED,貼上貼片,為選手除顫。
大概9時21分,倒地跑者眼睛眨了一下,呼吸、意識開始恢復,馬俊杰松了一口氣,“這是我十八年從醫經驗里,第一次使用AED。”這也是國內馬拉松比賽首個AED成功救人的案例。有意思的是,倒地者蘇醒后站了起來。還試圖繼續跑完全程。
“他的記憶還停留在,他往終點沖刺的場景里,當時發生的情況,他什么也不知道。”選手事后與馬俊杰回憶。
這一度引起很多人質疑,“當時很多人不相信,救護車過來,看這個人活蹦亂跳的,還能跑,不相信是心臟驟停的人,他們認為就是單純的暈厥,后來他就自己恢復了。
AED的芯片詳細記錄了AED從打開到使用至關機的全過程,數據出來后,一切了然,有人直呼“奇跡”。
這不是什么遙不可及的奇跡,“在賽道上,跑者倒地,心跳停了,如果你按照標準化配置,把他救回來,是很正常的事情。”王西富所言的標準化配置,便是救治上述跑者時使用的胸外按壓+AED電擊,在心臟驟停1分鐘內除顫,生存率可達70%這是急救“技能”的必修課。
“所以說,救回來的時候,不要說奇跡,根本不是奇跡,那是大概率事件。救不回來,我們反而要積極反思一下,我們的流程是不是要做進一步改進。”王西富再一次強調。
公開數據顯示,美國平均每十萬人配備317臺AED,日本平均每十萬人配備235臺,澳大利亞、英國、德國、香港地區,每十萬人AED配備量分別為:44.5臺、25.6臺、17.6臺、10臺。
不僅如此,美國政府每年提供3000萬美元專項資金用于實施公共除顫計劃,在急救車5分鐘內無法抵達的公共場所全部依法設置AED,鼓勵接受培訓的非專業大眾能隨時使用AED急救。
而中國,每十萬人保有的AED數量,趨近于零。陳朗時常覺得遺憾,“這么小的盒子按幾下就能救命,不難也不累,可這么好的東西我怎么從來沒見過?”
目前美國AED社會保有量超過150萬平均每兩百人共享一臺。按照美國標準,以上海兩千萬人為例,至少需配置十萬臺AED,但上海地區的實際保有量,僅為六百多臺,而這,還是“全國做得最好的。”
價格高,是AED難以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,但即使免費,推廣AED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普及AED難在何處?
2016年7月2日,在金波遺體告別儀式上,知名公益人鄧飛和金波的生前好友發起成立了“心喚醒”基金,稱將以金波的名義,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地鐵、車站、機場商場等公共場所添置包括AED在內的心臟驟停緊急救援設備,同時倡導和推動對這些場所的工作人員進行定期的專業培訓。
“心喚醒”一直希望,能將第一臺AED捐贈給金波倒下的北京呼家樓地鐵站,但幾番嘗試,至今未能如愿。最終,這臺AED設備在朝陽門附近的悠唐廣場落地。
“為什么是悠唐?”“心喚醒”聯合發起人張元春去到捐贈儀式才明白,“因為悠唐廣場的老板是日本人。他自己學過急救,在日本的企業也配備了AED,了解這個東西。”
呼家樓捐贈“失利”,張元春沒有灰心,“我就覺得,(心喚醒)機構對(地鐵)機構不行,如果你愿意,我可以以個人名義捐給你。”
他在自己的公號撰文,表達了捐贈AED的想法,沒想到,兩小時不到,已有廠家表示愿意無償提供設備。AED有了,但地鐵仍然沒有回應。
他選擇主動出擊,通過朋友聯系到北京地鐵負責宣傳的工作人員,一番交流,對方回應“這事不歸他管,他也不知道歸誰管,所以愛莫能助。”
“那你幫我問一下,誰來管這個事情你把聯系方式給我,我再去聯系。”張元春繼續追問。
“行,好的”,對方一口承諾之后卻再無回復。
幾經周轉,這臺AED最終捐給了清華大學陳明游泳館。
呼家樓告一段落,張元春仍不放棄。這一次,他將目標對準了北京宋家莊地鐵站。“第一,我家離宋家莊地鐵站特別近我可以提供培訓、維護。第二,那里三線換乘,客流量很大。”
同樣的,他先是發了一篇文章,沒有回應。之后,去到地鐵站咨詢,工作人員表示“沒有權限,需要找領導”。他確也曾找過兩次領導,不湊巧、領導都不在。
后來,一位地鐵站的朋友找到他,說可以幫忙牽線。張元春的熱情再次被點燃。很快,回信來了,“他說(地鐵)區站長很感興趣”。恰巧,一個AED廠家知道了這事,表示愿意提供設備。廠家將設備轉運至北京辦事處,靜待下一步信息。
幾天后,消息回來,區站長打退堂鼓但了,“他覺得,最好有上面的統一安排,而不是自己擅自做決定。”張元春理解他的難處,沒再繼續。而這臺AED,仍躺在廠家辦事處,繼續等待。
束之高閣的不止于捐贈未果的AED在不會用、不敢用、不讓用,使落地的AED大多也成了擺設。
媒體曾報道,為數不多的安裝于機場等公共場所的AED,被上了鎖,或貼一張義條:非醫療人員,嚴禁使用。“但恰恰AED就是給非醫療人員使用的。”田燃說。
在我國,AED屬于第三類醫療器械廠根據我國對第三類醫療器械的管理規但定,使用者必須是專業的醫療人員。這與AED“公眾急救設備”的定位確有沖突。
2017年1月10日,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布《體外除顫產品注冊技術審查指導原則》(以下歸簡稱“《原則》”),其中提及,“某些自動體外除顫器可由經急救培訓的人員使用。”
不久后,2017年3月15日,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》第184條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。《總則》規定,“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,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。”
這一善意救助者責任豁免規則,被稱作“好人法”。
《原則》與“好人法”的相繼發布,算是為AED普及掃清了一些路障,但急救科普依然任重道遠。“最大的問題還是公眾意識缺換乏”,田燃說。無論是CPR,還是AED,要讓公眾“會用”“敢用”,關鍵是配套的公眾培訓,意識上去了,方能有更多的人,“路見危難,伸出援手”。